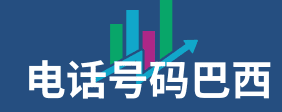由复兴党和阿萨德家族主导的叙利亚伊斯兰主义的破坏性潮流作斗争的现代化政权之一。复兴党由哈菲兹·阿萨德领导,从 1970 年代到 2000 年去世,将民族主义与泛阿拉伯主义情感融为一体。复兴党的世俗社会主义议程使该党国与穆斯林兄弟会叙利亚分支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在 1982 年的冲突中被残酷镇压。作为其父亲的继承人,巴沙尔·阿萨德起初谈论改革,但自 2011 年以来,他一直在与组织松散的武装反对派(包括著名的圣战组织)为生存而战。内战重新提出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不仅是伊斯兰教在叙利亚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作用,而且是哪种伊斯兰教版本应该占主导地位。在叙利亚和其他地方,答案各不相同,这取决于你是在城市还是乡村询问,也取决于你是询问逊尼派、什叶派、基督教徒、阿拉维派、德鲁兹派还是库尔德人。
复兴的伊斯兰教所提出的问题与
民族主义争论的主题十分契合。爱德华·赛义德警告不要以“抽象”的眼光来思考该地区,因为这 电话号码库 “几乎无法让我们了解自己或进行明智的分析”。2001 年 10 月,他在《国家》杂志上发表文章称,文明和身份不是“封闭的实体”,而是持续不断、多方面的意识形态冲突的领域。如果美国领导人接受这一关于现代世界的普遍真理,他们可能更有机会对叙利亚问题进行“明智的分析”。应该清楚的是,局外人可以试图影响民族主义辩论,但他们不太可能对辩论的条件和合法性有太多了解。
叙利亚起义
就像民族主义一样,帝国主义给叙利亚
危机和该地区蒙上了一层阴影。美国、英国和法国都与殖民主义、军事干预和文化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他们没有因为支持独裁者、偏袒以色列和培养对政治伊斯兰的厌恶而赢得任何赞誉。美国处于特别不利的地位。虽然奥巴马坚称(就像他在 2009 年开罗演讲中所说的那样)美国不是“一个自私自利 的营销计划中使用内 的帝国的粗俗刻板印象”,但历史记录强烈反对他。从埃及和巴勒斯坦到伊拉克、伊朗和阿富汗,英国霸主在 1945 年后屈服于一个拥有更大财政资源和军事实力的新兴大国的主导地位。美国人不仅追随英国的脚步,而且总体上继续实施间接统治的战略,偶尔发动政变、不时进行平定运动,偶尔进行炮舰外交。这种方法降低了帝国的成本(对于虚弱的英国来说尤其重要),但它也避免了更明显的帝国直接统治(这与美国的自我形象明显不一致)。
叙利亚是过去一个外来干涉被铭记、憎恨和抵制的变种。阿萨德在今年的一次采访中将帝国与“分而治之”战略联 邮寄线索 系起来,这可不是随口说说。“我说的分裂,不是指重新划定国家边界,而是指身份认同的分裂,这要危险得多。”这种对帝国遗产的执着——经济、政治和文化——是整个地区的现象,从 2013 年 7 月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来看,美国的政策显然存在问题。相当一部分受访者断然宣称美国是“敌人”,而不是“伙伴”。土耳其、黎巴嫩、巴勒斯坦领土和巴基斯坦约有一半到四分之三的人持这种观点,埃及和约旦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持这种观点。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敌人”的回答比例都超过了“伙伴”的回答比例。